
2022年春节档,电影《奇迹·笨小孩》在同档期众多竞争对手中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不错成绩。自《我不是药神》以后,文牧野似乎掌握了一套讲述现实题材小人物故事的创作方法:故事工整、节奏准确,着力于刻画小人物群像,突出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结。《奇迹·笨小孩》也延续了《我不是药神》的剧作模式,讲述了以景浩为代表的“小人物”们在生活的重压下历尽艰辛、最终成功的励志奋斗故事。同时,影片又明显受到《当幸福来敲门》这类好莱坞剧情片的影响,对于叙事节奏、人物关系的把握和处理显得十分娴熟。
从这个角度而言,《奇迹·笨小孩》是很适合春节档的成熟剧情片,甚至可能是这个春节档内除了动画电影之外最“合家欢”的剧情片。一方面,借由深圳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故事空间,影片恰到好处地触碰到了一部分社会现实议题,通过对小人物群像的刻画传达了现实关注。另一方面,这些现实关注几乎从未脱离中产观影人群的“小人物想象”,而“奇迹”故事不可避免地将其进一步消解,最终搭建起一个励志、温暖的核心框架。
以情为驱:
创业故事的情感表达
《奇迹·笨小孩》在剧作上可称是小人物励志剧情片的范本,工整得可以在编剧课堂上进行“节拍拆解”。
主人公景浩在母亲去世后与妹妹在深圳相依为命,从大学辍学成为了一位手机修理师傅。为替妹妹筹齐手术费,景浩尝试翻新机、零件拆卸零售等赚钱方式却屡遭重创,走投无路之际,景浩孤注一掷赌上所有积蓄,最终在伙伴的支持和帮助下历尽艰辛、获得成功。故事背景被设置在深圳,这一城市空间带有太过强烈的象征意义,几乎不可能与“改变命运”“创业”“奋斗”等关键词切割开来。外来务工人口正是深圳的标签之一。在深圳的地铁上,能够轻松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方言,而影片中屡次出现的几组城市鸟瞰镜头,则有意将深圳刻画为一座镜像之城。“上层”的CBD里,高耸威严、窗明几净的高层办公楼林立,而“下层”的城中村等地区,则密布廉租房、小商铺。可以说,深圳的地方性为影片的真实性提供了最重要的现实基础,也借由镜像般的城市影像树立起一组剧情内未必着重强调的对立关系,为讲述大城市中的“小故事”奠定了现实基调。影片中,网吧大神等具有现实关注度的场景和类型人物也带有明显的“深圳特色”,而片中屡次出现的蝼蚁符号则不断昭示小人物的命运——卑微、弱小,但坚忍不拔。
尽管影片本质上是在创业之城讲述创业故事,但不同于同类题材影片惯常以“追梦”“奋斗”为宏大主题,《奇迹·笨小孩》尝试把景浩的人物动机落在亲情上,有意地弱化了景浩希望改变命运、出人头地的野心,使得影片看起来不至于太过“成功学”,转而以兄妹之间的羁绊打动人心。“情感”也由此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叙事线索,也是影片中的小人物得以在大城市中生存甚至完成“奇迹”的唯一仰仗。在影片中,兄妹情、忘年交、伙伴情谊等一系列情感维系,不仅基本连接起所有人物的动机,也构成了情节上最主要的几处转折的合理性:一是梁叔几无条件地帮助景浩开始“创业”,包括后续钟老的“入伙”,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熟人社会”式的邻里情;二是景浩等人替汪春梅出头,一场“群架”在叙事上完成了团队建制,是侠义式的拔刀相助,在此段落后的婚礼情节,更是对团队成员之间类家庭情感的一种渲染;三是景浩对赌任务濒临失败时团队好友的鼎力支持,则是典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情感叙事。除主要人物外,章宇饰演的高空作业队队长和田壮壮饰演的门卫爷爷,也被赋予了天然的善意。这几种本土化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情感类型,贯穿了《奇迹·笨小孩》故事的始终,成功地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与共情。
剥离现实:
“笨小孩”的“奇迹”何以可能?
不过,《奇迹·笨小孩》中的情感叙事固然动人,但同时也是高度假定的,仍然服务于个人奋斗的内核框架。对比人物背景类似的影片《我的姐姐》,《奇迹·笨小孩》以一种近乎虚构的方式切断了失去父母的少年兄妹/姐弟可能面临的真正的现实问题,直接将兄妹两人从繁琐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土地关系中剥离出来,以保证奋斗故事的完整性。尽管易烊千玺贡献了相当精彩的表演,景浩这一角色仍然带有一种悬浮感——他所对抗的基本上不是非法组织就是极端天气,从开头的翻新机政策到台风、再到被违法炼金组织偷走零件,景浩要面对的大都是偶然性很高的外部干扰。而他自身的境遇,以及真正有力度的难题则被大幅忽略了,最终留下的只有房租这一浮于表面的困境表达。妹妹景彤则基本成为只负责提供情感输出的工具角色,几乎完全缺席主要叙事。
同样,影片中其他人物的设计尽管涉及包括三和大神、务工人员、工厂维权女工等现实形象和社会议题,但也都因服务于奋斗故事的内核而流于表面,成为了一个个标签。与景浩景彤兄妹类似,其他人物也在团队建立之初就迅速地从生活场景中被拔了出来,进入了好景工厂这一多少带点假定性的工作空间。此后,大部分人物关系的建立和变化也在这一场景中发生,观众基本无从得知角色们的生存现实,人物群像的现实底色也都被景浩一手建立的工厂所替代。失去生存现实的角色们也失去了生活质感,只能靠被“困”在工厂内的人物关系和情感连接来塑造人物。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物给予景浩的善意也几乎是无私而无后果的:梁叔可以轻松抛下福利院的白班工作,队长可以给景浩多开工钱,刘恒志的妻子也可以开着工作吊车来援助……正因为角色的生存现实被隐藏了,这些善意本该因为现实的高昂代价而显得珍贵,在影片中的给予却过于轻松。
从创作角度,完全能够理解这些情节的技术合理性。在《我不是药神》中其实也出现过相似的问题,只是被影片题材本身的特殊性所中和了。但是,如果《奇迹·笨小孩》对草根生活的可贵传达正是立足于表现不完善的福利保障下个体生存的不易,那么这些轻易赋予的善意削弱了影片的真实性,使得景浩作为小人物的境遇变得个人化、特殊化,可谓遗憾。尤其当影片结尾,景浩以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台上而众人都以公司职员的形象坐在台下时,我们很难不产生“情感被剥削”的违和感。
诚然,《奇迹·笨小孩》是合格的春节档励志剧情片,而观众永远需要温暖、希望和感动。但是,如果“奇迹”只能依靠纯粹却失真的情感关系来实现,“笨小孩”的讲述是否会止步于满足城市中产观众的对小人物“咸鱼翻身”的想象,而从未碰触真实?
(尹一伊 作者为传播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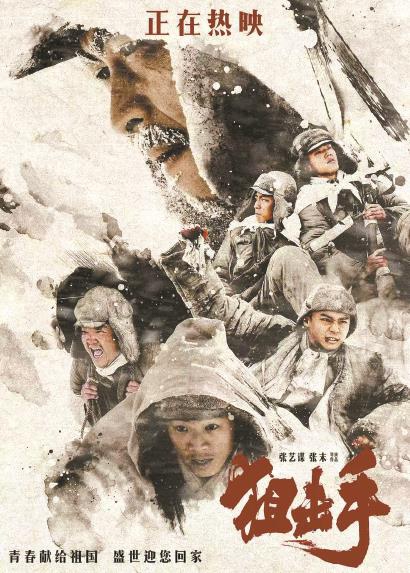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