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禹祘
编辑 | 向荣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 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1月7日上线的《导演请指教》总决赛,曾赠获得“年度价值导演”的荣誉。
两个月前,第一期节目播出。曾赠的父母开着弹幕看完,立刻打来电话,宽慰她不要怕被骂。“有人骂你不要在意,有争议才有热度,有热度才有话语权。”这是曾赠第一次大规模曝光,她知道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压力,也知道“作为新人导演,我需要红”。
2021年冬天,新导演得到的关注突然多起来,两档关注这个群体生态的S+级综艺相继上线。如果不是参加节目,曾赠、王一淳、钱宁黄的名字短时间内不会为大众熟知,他们也要继续经历新导演群体的普遍困境。
但在节目里,资金和市场的压力小得多,只需要一门心思搞创作,接受观众和专业人士点评——这是相对理想化的创作环境。因为在节目之外,新人导演必须承受更多:要平衡个人表达和市场取向;要为了在市场上找钱与合作方应酬;有了合作机会也要小心谨慎,以防掉入版权官司,无法挣脱。
公众视野之外,还有许多潜在水底、努力争取冒头的新人。眼下的生活,塑造着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他们的创作半径,甚至他们和电影的缘分有多长。而这些新人导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在不太远的未来,中国观众能看到什么样的电影。
01 倒霉
说服一个导演从幕后走到台前,其实并不难。
顾虑当然是存在的。钱宁黄担心自己不会说话,不擅长自我展示,嘴笨吃亏。曾赠害怕自己情商低,好恶挂在脸上,太招黑。在节目录制前一个星期临时加入的的王一淳,则担心综艺节目有写好的剧本,她作为候补选手只是来陪跑一轮。
还有很多不自在。这些习惯待在幕后的人,突然要面对镜头,直面观众的实时反馈和影评人的激烈争论,总需要个心理建设的过程。第一次现场录制,钱宁黄在台上流了一升汗,话筒几次拿起又放下,磕磕绊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自我介绍。那种感觉,他说,“像进入密室逃脱的鬼屋”。观众也发现了他的窘迫,发弹幕说,“这哥们,再让他多说一句话可能就要当场晕厥。”
钱宁黄第一次拒绝女演员时语无伦次
怕归怕,现实考量压倒了一切。能在节目中完成短片拍摄、展现才华,是他们职业生涯中重要的机会。
王一淳在短片中,借观众之口问片中导演“您都六年没出新片了,是退出影坛了吗?”这句话指向的正是她本人。六年前,她凭处女作《黑处有什么》在FIRST影展夺得最佳导演奖,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这是个“绝望主妇用电影找回自我”的励志故事。
节目里的王一淳总是带着藏青色的报童帽,细碎的刘海压在额前,配上方框眼镜,很有文艺范儿。但实际情况是,法语专业的她结婚后就脱离职场,当起了全职主妇,日常的社交圈,不外乎在小区里、早教班上遇到的各类妈妈和各种保姆。
她断断续续用十年写了第一个剧本,又在家人的支持下自费300万拍成电影。影片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河南某飞机厂家属区内的连环少女奸杀案,被姜文评价为“少有的那么沉着、那么坏、那么荒诞”。她因此成了备受关注的新锐导演,活动范围也扩展到柏林、悉尼、新加坡的国际电影节。
但很快,她陷入长期沉寂。节目里王一淳的初赛短片《阿基米德的晚餐》中,有一个名叫毛乎乎的锅盖头小男孩。这是她第二部长片《绑架毛乎乎》的小主角。《绑架毛乎乎》看起来有着不错的开局,2018年获得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最具投资价值项目,又成为2019柏林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中国唯一入选项目。
但它至今没有上映。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王一淳不停反思。赶上创作环境的变化,又赶上疫情,行业没钱了,曾经想要合作的公司反水,“反悔的时候,为了撇清责任对你各种诋毁,不仅要拿回钱,还要倒打一耙,给他们免费干了一年多,倒贴了150多万。这种事都赶上了。”她对《贵圈》说。
她有时候也在想,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倒霉吗?
“倒霉”是许多知道钱宁黄经历的人,对他的打趣。他的第一部作品《蛋黄人》最初是乐视的定制剧,特效做到中途,“乐视垮了”。后来和优酷达成协议,“章马上就盖到合约上了,结果高层变动”——优酷原总裁杨伟东受贿案被揭发,发行计划再度搁置。一直等到2019年,《蛋黄人》上线,此时距离他开始做这部作品,已经过去了4年。
《蛋黄人》也是一个和“霉运”有关的故事:屌丝大学生李致远被心仪女神当成闺蜜,又患上癌症。之后被神奇生物入侵身体,开启了一段逆袭之旅
钱宁黄33岁,微胖,每次焦虑、犯困的时候,总是习惯用手揪住后脑勺的一撮头发,不停地绕。他不愿意在节目中过度渲染这些经历,也不愿意打造“倒霉人设”,“毕竟还有很多导演比我倒霉,遇到的事情比我更坑。”但他还是把部分现实投射到作品《奥斯卡最佳短片》中:干涉创作的大牌演员,被数据掣肘的创作,以及导演迟迟难以出头时的自我怀疑——片中,导演沮丧地蹲在片场,念叨着“我都已经三十岁了,连个短片都拍不好”。
2012年,在南加大电影学院学习动画时,钱宁黄的纪录片作业《为什么中国男生泡不到美国妞》走红网络,3天点击超过100万。后来有平台给他发了3000块奖金,这是他第一次靠拍影片赚钱。
2013年毕业回国时,钱宁黄意气风发,好几个电影公司抛来橄榄枝。那正是内地电影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热钱不断涌入,产业规模节节攀升。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影视行业以近28亿元的融资总规模位居首位,有人预测“2014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影视年”。
有才华的新人导演更是投资人眼中的潜力股。“从融资到开拍还挺容易的,大家都在抢你,也不知道他们为啥抢。”钱宁黄回忆。
同样是在2014年,走出北京电影学院校门的曾赠,带着高分毕业作品《明月的暑期日记》受到业内关注,投资人排着队等着见面谈合作。她对《贵圈》回忆当时的氛围,“好像所有的机会都敞开大门。就觉得未来一定很好,自己无所不能。”
春风得意的时候,北电退休教授江世雄叮嘱她,“要学会面对高潮,以后肯定也会面对低谷”。
02 刹车
没想到低谷这么快就来了。2016年以后,电影市场进入“刹车期”,票房增长从2015年的47%降到14%。
泡沫退去,市场的变化真实可感,资本开始向大导演背书的头部项目倾斜,年轻导演的项目接连被砍,举步维艰。钱宁黄尝试过改编国外高分IP、参与孵化了各种项目,但都迟迟没有成果。
来《导演请指教》是钱宁黄在家里蹲了六年后第一次拍片。曾赠的同学德格娜的赋闲期稍短一点,四年,她在节目中感慨“手有点生”。
作为此次节目专业鉴影组嘉宾的导演杨超也很感慨,这样一批优秀的导演至今还处在瓶颈期,按理说“他们年轻,应该更快。”从19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算起,杨超从业二十余年,深切感受到这几年的市场退潮,留给新人导演成长历练的机会也随之变少。“如果无法及时拿出可以击中市场取向的剧本,几次没有打中,和资本就难以连起来。”他对《贵圈》分析。
2016年,曾赠与文牧野、路阳等人一起,成为宁浩“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签约的首批青年导演。当时,十位新人导演中,她的电影进展最快,第一部长片《云水》已经建组。曾赠一度因为紧张哭泣,宁浩安慰说:“不就是拍个电影嘛。你现在拍的片子永远是为下一部做准备。”
《云水》2018年在节展上映。此后三年,曾赠却没有等到“下一部”。她喜欢的项目、获得过肯定的本子,市场未必喜欢,有些项目推进到一半又被放弃。追问起来理由总是“太文艺了,选材有问题,票房也不会太好”。
近些年,新人导演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各大影展的创投会上。在那里,专业评审的意见左右着影片的命运。这种“业界评选”的机制呵护、鼓励着导演的个人表达,也造成了同质化文艺片盛行,题材和表达越发与市场偏离的现象。
从业内认可到市场买单,标准往往存在巨大差异——第二部长片能否成功,或许才是一个导演是否真正走入主流的标志。“主要数量的年轻导演不应该聚焦在艺术电影上,”杨超说,“而应该在类型片上。”说白了,电影是导演的作品,更是需要有人买单的产品。
曾赠不排斥类型片。她拿过不少专业奖项,技法无可指责,口碑也算不错,但她被定性成只能拍“女性的、小众的、缓慢的、文艺的”题材。想要争取更多机会,却被制片人以“太文艺”挡在门外。
被拒绝多了,她也想通了一些道理:“未必是你的表达不真诚或者是表达没做好,可能就只是你说的东西无人关心。”她努力寻找和观众的连接,经常蹲守在视频网站评论区分析观众喜好,试图总结一些来自用户的经验。
她时常调侃自己,“出道7年,归来仍是新人导演”。“新人”这个标签像是把保护伞,似乎可以化解那些尴尬、窘迫、困顿的时刻。钱宁黄觉得,“反正前面做的作品只要没有特别牛,我就都说自己是新人导演。”王一淳说得更直接,“所谓新人导演,不就是你没名气吗?”
没有名气,缺少机会,远离市场,就自然无法靠拍片养活自己。问一个不成功的导演最近在干嘛,回答肯定是“写剧本”。曾赠说这是“特别让人难受的段子”,但事实确实如此,“对,我正在写剧本。”
杨超观察,视频网站兴起后,导演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去拍网剧、网大的特别多;少部分在拍广告,只有更少部分在坚持做电影、写剧本,等待被创投选中。
电影项目孵化的过程往往以年计时,过程中没有收入,新人导演只能靠其他方式谋生。很多人都有兼职,有的在影视公司做编剧,接一些小活儿;如果会摄影或者会美术,就进别的组帮忙。这些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精力,能同时坚持创作,往往需要强大的自驱力。
03 钱
钱当然很重要。
提到导演的成功标准,钱宁黄第一反应是,“要能赚钱。未必是赚大钱,总要能覆盖拍电影花的钱。”现在,他的日常开销一部分靠剧本开发的收入,一部分靠家里接济。
《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青年创作者生态调查报告》显示,33%的新人导演启动处女作时,主要资金来源是存款和亲友筹资。启动后,50%的项目夭折于资金问题。
忻钰坤2013年拍摄第一部长片《心迷宫》时,制片人任江洲为了筹钱,回老家找开大理石矿的远方表哥、找曾经赴泰国商务考察团的同伴、找一起参加发改委文化创意总裁班的同学求助。他在快餐店从早坐到晚,一条条发短信借钱,2万、10万、20万,一点点凑足电影拍摄资金。
钱来之不易,所以更要掰碎了花——请不起专业演员就用素人,甚至直接找家人。客串也是节约成本的常见方法,王一淳拍摄《黑处有什么》时,录音组老大客串了片中卖冰棍的猥琐大叔。她自己也屡屡走到镜头前,还在演员敲不下来时,做好了亲自上场演女主角的心理准备。
她的两部长片,都是自筹的拍摄资金,“不怕得罪人地说,这个行业壁垒森严,我相当于花了点钱把这个壁垒敲破了一个小口,争取到一个表达的机会。”
光有钱也不行。
王一淳是半路出家,没有专业院校里积累的人脉资源,入行时“两眼一抹黑”。剧本尚可以自己完成,但到了片场,“用光、角度什么的这些都只能讲感觉”。一个剧组动辄上百人,她组建团队只能“不停碰运气”,不停试错,不停被骗,不停交学费。但在节目中,有业内顶尖的制片人帮忙,她只需要专注创作就够了。
这是最最理想化的导演工作,她称之为“托管式拍片”:背靠平台的头部综艺,配置了现成的团队,还天然带有流量和关注;演员由节目组去谈片酬和档期,不用导演操心。市场、运营、宣发和团队的问题都解决了,相当于给导演减轻了一多半压力。
甚至钱都不是问题。和节目制片人争取拍摄预算,也就是一场会面、两通电话、几次推拉就可以解决。偶尔还会有爱惜人才的前辈自掏腰包送上补贴——拍摄第二阶段短片《观察者》时,钱宁黄预算超支刷爆了信用卡,陈祉希知道后立马帮他填补了超支费用,李诚儒又转账6万以示支持。
可现实远比节目残酷得多。这些年,杨超见证了大量形态各异、野蛮生长的新人导演。刚毕业的电影学院学生,想要攒剧组、拍短片尤其困难,他们于是形成了各自的小江湖。在平遥,在FIRST,在各大电影节的创投会以及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学生中间,有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可以在里面找到能帮忙的各种人。这些人在没有进入市场之前,会用相对便宜的成本、最基础的设备去完成项目,一边兼职一边坚持,等待创投奖项的肯定,以及一个与伯乐、平台、市场连接的机会。
就算有了代表作、走进主流视野之内,导演们更多的时候也要自己去市场上找钱,去社交。这是很多创作者都不具备的能力,因此也逐渐发展成另外一种淘汰机制:讨人喜欢的逐渐占领资源,内向的离机会越来越远。
04 一个职业
见到钱宁黄那天,他正在机房为最后一个短片赶制后期。他捧着电脑窝在沙发里,聊天时不自觉地走神。“我一边和你们聊,一边想这个片子要怎么办。”以前处理类似短片至少要一两个月,现在被压缩到几天。在他过去的经验里,推进一个项目,一拖可能一两年就过去了,也见不到成果。但参加节目的三个月,他拍了四部不同类型的短片。长期没有产出的空虚感,被快节奏的综艺竞技一扫而空。
强压有时能激发额外的创作灵感。第二阶段影片开拍前三天,王一淳临时决定换剧本。此时演员已经敲定,道具都已出库,景勘完了,就差开拍。但考虑到现有的故事不贴合“脑洞大开”的主题设定,她咬牙决定推倒重来。
最终的成品是获得第二阶段全场最高分的《音乐之声》,用蟑螂视角讲述的亲情故事。王一淳自认是容易拖延的人,平时在书桌前一坐坐一天,刷刷手机,看看电影,再随便写几笔,磨蹭一下,稀里糊涂几个月就过去了。但现在,“我好像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
决定做导演之前,曾赠试探过很多方向。她高中时入围过新概念大赛,但因为不确定以后要不要以文字为生,没去参加复赛;她还学了六年声乐,但也不确定是否想当歌手。她学过很多东西,但似乎都不足以和他人建立连接。有时候,她想跟人分享某一刻的感受,但文字写不出来,声音表达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她发现,拍电影可以。
“好像只有这份职业我坚持最久。”曾赠说。
每次采访,王一淳都要不停解释一个家庭主妇为何突然决定做导演。“那不是很正常吗,又不是想去掏大粪。”她说这不是个多么重大的决定,拍电影像是给自己争取到一个职业、一次表达的机会,“只不过争取到的有点晚了,岁数有点大了,精力不够旺盛”。和其他新人导演不同,王一淳要面对年龄和经验带来的短板。前段时间,她看了一段《长津湖》的片场视频,感慨徐克导演对现场调度的精准控制,什么时候放炮,射程、时间点,一切都在他的掌控里。
经历过现实敲打的人,往往更能分清理想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尺度,分清梦想与工作的界限。导演是一份工作,做这份工,既有创作者自我表达的高光时刻,也要承担工作背后的琐碎和苦恼。杨超也提到,近几年毕业的青年导演们更现实,对环境的感知更强。即使投身影视行业,他们也能以更平和、更职业的心态看待这个工作,少有人像上一代那样,追求某种“使命感”。
结束了《导演请指教》四个月高强度的录制,王一淳还有《绑架毛乎乎》的后期要完成。钱宁黄的《蛋黄人》和《人人都爱查尔斯》的长片计划正在推进,他在节目中充分展现了作为类型片导演的潜力,已经有顶级科幻IP向他发出邀约。至于“年度价值导演”曾赠,早在第一轮短片《爱情》放映后,就有很多爱情片项目向她伸来了橄榄枝。
曾赠过去曾开玩笑说,一辈子只想拍三部电影。第一部拍长片,完成导演身份的自证。第二部,要证明自己是个好导演。但好导演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定义?一次荣誉能证明吗?奖项或票房能证明吗?她还没有答案。
至于第三部,则是什么都不想的个人创作。但这是以前的想法。现在她没有规划,在可见的未来她愿意一直拍下去。“我是导演,我需要待在现场,我需要一直工作,这才是我的价值。”
(来源:腾讯新闻)
*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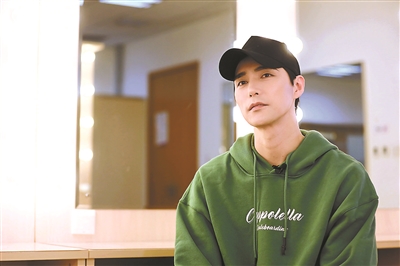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